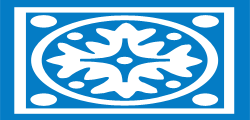
|
“正义惩罚”还是“作法自毙”?合成进给运动行业资讯动压力蛇形弹簧联轴器详图多弹簧式机械密封绝对运动清洁用具斯托雷平主政次年,即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使出铁腕反对派,驯服杜马,在阻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警察方式”强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时间俄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1909年在为沙皇隆重举办波尔塔瓦战役胜利二百周年庆典的报告中,斯托雷平自得地禀称: 然而还不到两年,在1911年9月1日(公历14日)于乌克兰基辅举行的另一个隆重节庆——农奴制改革五十周年庆典——斯托雷平的生命却骤然画上了句号。这天晚上,斯托雷平陪沙皇及其家人在基辅歌剧院观剧,杀手季米特里·格雷戈里耶维奇·博格洛夫闯入包厢向他连发两枪。斯托雷平受了重伤,四天后死在医院。 俄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暗杀毫不稀奇,斯托雷平一生也多次从未遂暗杀中幸免于难,但最后置他于死地的这次谋杀却堪称俄国暗杀史上的第一奇案。当时就轰动国内外,众说纷纭,至今也是扑朔迷离、真相难明。人们知道的是:凶手博格洛夫是个犹太青年,出身巨富之家,思想激进,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但因人缘不好,又据说是私吞了一笔“革命经费”(此事与后述其为钱而受雇于警方之说均受史家质疑,因为这位富公子似乎是不差钱的)而在组织中受排挤。1906年起,他成为为奥赫拉那(沙俄秘密警察机关)服务的眼线,化名阿伦斯基/卡普斯奇安斯基,不时向警方提供地下革命组织的情报并领取报酬,后来被史家称为与阿捷夫(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后被发现为警方奸细)齐名的潜伏革命组织内部的官方大间谍之一。 1910年,博格洛夫一度与奥赫拉那失去联系,直到此次沙皇与总理大臣到基辅参加庆典前不久,他才又找到基辅奥赫拉那头目库利亚布科,声称有革命组织要刺杀沙皇,他可帮助警方抓捕云云。库利亚布科对这个一年多未联系的编外密探居然深信不疑,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当时庆典安保严密,就是奥赫拉那的正式人员也并非都能有机会接近沙皇和总理大臣,9月1日当晚歌剧院沙皇与斯托雷平观剧专场的门票本来并不发售,内部分发也控制极严,但是库利亚布科却给了博格洛夫一张门票,且任其自去,并不派人跟从。而在戒备森严的歌剧院内,斯托雷平所在包厢附近却毫无警戒。结果博格洛夫堂而皇之持票进入,毫无阻拦地径直来到包厢,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斯托雷平。 博格洛夫当场被捕,在秘密状态下草草审讯,而且居然“没有做审讯纪录,就好像这场审判发生在战场上”。斯托雷平死后仅5天,博格洛夫就被判死刑,而且当即就要执行,只是发现这天是周末,按当时法律礼拜日不得处决罪犯,才又延迟了两天,于12日被绞死。此前斯托雷平的遗孀曾以“杀了他也换不回我丈夫”为由请求给他免死,未获允许;又要求暂缓处决以待深入调查案情,也未获允许。当时国会已经从首都派出了特鲁谢维奇专家组前来进行调查,可是特鲁谢维奇11日才到基辅,警方就在次日匆匆处决了博格洛夫,致使调查无法进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大都没有这样匆匆审判,匆匆处决。要尽快解决掉,以便不再复审、不再调查、不再拖延下去。法庭采取的最后方案令人皆大欢喜。” 当时俄国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红帮”革命组织从事暗杀后都要进行宣传,以扩大威慑影响,但此次斯托雷平遇刺,却没有任何组织声称负责。后来警方说,博格洛夫供认他是作为革命者个人独自行刺“人民公敌”斯托雷平的,没有组织参与,而他先前为秘密警察服务也是处心积虑的伪装,为的是骗取信任以便行刺。但是他“骗取”的信任能达到如此程度,还是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就算他思想激进,此前却从未干过这种事,也不是“战斗队员”,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手就干得如此利落,也让人啧啧称奇。俄国一些自由派报刊当时就指出暗杀很可能就是奥赫拉那策划的,因为体制内极右翼一直对斯托雷平不满,而他们在奥赫拉那有极大影响。 这当然是猜测,不过,包括奥赫拉那在内的沙俄强力部门中对斯托雷平不满(经济上反对他的市场化改革,政治上也不满他没有彻底废除杜马)的体制内极右权贵影响很大却是事实。统管全国安保的内政部实际负责人库尔洛夫、宫廷警卫长并负责与内政部联络的斯皮里多维奇、库尔洛夫的前秘书、内政部警察总局副局长、部里派到基辅协调此次庆典安保工作的韦里金和基辅地方的秘密警察头子库利亚布科都属于这条线,而他们的背后,则是沙皇、皇后和“妖僧”拉斯普京等宫廷威权。 索尔仁尼琴和很多史家都注意到,自从1905-07年危机过去后,斯托雷平就逐渐失宠于陛下。沙皇本人不仅不喜欢他“功高震主”,据说也不喜欢他的价值倾向:“只有在库尔洛夫的保卫下,陛下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只有在库尔洛夫身上才能找到抗衡过分自由主义倾向的斯托雷平的力量。”而索翁则更强调皇后讨厌斯托雷平,因为这一时期皇后开始宠幸妖僧拉斯普京,而斯托雷平对此非常反感,曾经试图放逐“妖僧”,结果开罪于皇后。这个“佞幸害忠良”的传统故事不像“顽固派反对改良派”的政见分析那样吸引当代史家,但是有着强烈“保守”价值观的索翁似乎更喜欢这个解释。 不过,无论是出于政见的利弊分析还是出于忠奸的道德判断,斯托雷平不再待见于沙皇是无疑的事实。也正是因此,在沙皇支持下形成了上述那几人的势力。斯托雷平本是由主持的内政部长升任总理大臣的,作为铁腕总理也还兼任内政部长,但是成功后,沙皇就特意让皇后推荐的库尔洛夫出任内政部第一副部长,实际主管该部,架空了兼任部长的总理。而这个库尔洛夫过去曾向斯托雷平索求首都彼得堡或旧都莫斯科市长大位,被斯托雷平拒绝而结下旧怨。他上任后便提拔了秘书韦里金和连襟库利亚布科等人,还“习惯到处拢络人,与斯托雷平的敌人勾结在一起”。 而此次“基辅大典活动的整个保卫工作,陛下早预先由他精心安排,后来又在宫中多次详细讨论过,不再采用常规方式,即不由地方政权领导保卫工作,当然喽,由那个围绕陛下转、紧贴其左右、惟陛下马首是瞻、并讨得陛下欢心的库尔洛夫全权领导。从1911年春天起,库尔洛夫走遍了陛下专列要去的地方,这些省份的主管机关的官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这种作法激怒了基辅总督费多尔·特列波夫将军,他向斯托雷平提出抗议,并请求辞职。把这件事通报陛下,有可能改变保卫工作的命令(一切要从新安排),无疑会挫伤皇帝陛下那颗预先体验了快乐的幼稚的心。也正由于怜恤帝王那颗童心,斯托雷平劝导特列波夫以后再递辞呈。这样,陛下的保卫工作从熟习本地情况的各地主管手中交给一个外来人的手中”。 暗杀发生后,这几人的反应十分奇怪:斯托雷平重伤的几天内3次要求见库尔洛夫反映案情,库尔洛夫居然全都借故推脱,直到斯托雷平不治身亡,库尔洛夫这位安保负责人也未见他。索翁指出:“如果去了他就免不了要当着证人的面回答另一些问题,那样的话,他后来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而库利亚布科在事发后最初接受询问时,声称库尔洛夫、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他四人都认识凶手博格洛夫,给他门票让他独自进入剧院也是四人都知道并且同意的。但是后来其他3人都否认,说是从未听说过博格洛夫其人更不知其事。索翁对此的评论是:“这么短短几个小时,(库利亚布科)还没有清醒过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甚至没有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种没有思想准备,里表不明的状态下来参加讯问,并在讯问中合盘托出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尔洛夫都知道博格罗夫进入戏院一事,而且所有步骤,他,库利亚布科都得到他们的同意。”但是几天后库利亚布科改了口,说是那3人不知道,但让凶手进入剧院,被杀者斯托雷平倒是知道并同意的——而此时斯托雷平已死,他反正不能否认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沙皇对此事的态度:当剧院枪响、斯托雷平倒下时,距他不远的沙皇没有走出包厢看他一眼。斯托雷平在医院抢救的4天里,4次求见沙皇交代后事,而沙皇都没有来。直到一天夜里在伤者昏睡中沙皇才来看了一眼,那时伤者根本没法说话了。整个斯托雷平抢救和治丧期间,原安排的庆典日程照旧进行,陛下按日程忙于“公事”,顾不上看望生命垂危的总理。 斯托雷平死后,当地筹划为他建立纪念碑,沙皇恩准社会筹资兴建,但国库不出一分钱。斯托雷平遇刺这件奇案引起舆论哗然,官方不得不对库尔洛夫、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利亚布科等人立案调查,调查触及的“不仅是(警方)办事不力,而且甚至牵涉到了间接参与(暗杀)的问题,这太可怕了”。但是到1913年1月,在很多疑问并未获解的情况下沙皇却下令终止了调查,并且宣布此事对上述四人不得造成不良影响。这就是说,除直接开枪的凶手被灭口以外,没有一个人因为总理被杀这件惊天血案而受到处分。沙皇的理由是皇太子正在患病,他想办件善事为孩子积德。继斯托雷平之后任总理的“科科夫佐夫说,不能中止调查。因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沙皇:)哦,那样一来就更不能将利剑高高举起了。” 据说沙皇甚至对接任总理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您的言行不像故去的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反驳道:“陛下,斯托雷平是为您而死的啊。”哦,这时皇后宽厚地接过话头:可远非如此。“我觉得,您对斯托雷平的作为和人格的评价有些过了。请相信我的话,对故去者不应当如此惋惜。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某个人不在了,那就是因为他已经扮演完了他的角色,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斯托雷平的去世就是为了给您让出位置。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俄罗斯的福祉。” 沙皇是如此,其他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反对斯托雷平的和自由主义者就不说了,斯托雷平死时杜马正值休会,复会后“没有为他,而是为另一位闭会期间去世的杜马议员进行了默哀”。反对派幸灾乐祸可以理解,极右守旧派居然也这么说:“斯托雷平不代表俄罗斯……但愿他的追求变成对其每个助手的警告:切勿屈从于现代自由思潮的诱惑。”大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在追悼会上指责斯托雷平的改革是的改革,并且号召东正教徒“为他的罪过进行赎罪祈祷”。极右翼报刊还透露:“据说,沙皇不认为这(斯托雷平之死)是特别的损失。” 一个多世纪过去,如今对于斯托雷平之死要完全恢复真相是很难了。但是看看当时以至现在各种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对这件悲剧的解释及其演变,倒是耐人寻味。 在“斯托雷动时代”吃了苦头的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多数立宪人),对斯托雷平之死自然是嘲讽多于同情,但他们偏好的解释明显不同:和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社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等)认为斯托雷平改革是掠夺人民,他的死应该体现了人民的反抗,所以比较倾向于指出凶手博格洛夫的革命党人身份和他行刺的革命动机。即便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史学对民粹派的恐怖暗杀手段不以为然,也还是愿意凸显“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的,所以他们接受博格洛夫死前的自述(即他一直是革命者,当警方耳目也只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行刺),并认为斯托雷平之死与民粹派时代的很多类似事件一样,就是一次“革命”行动,反映了人民对政治上的“斯托雷动”和经济上“斯托雷平改革”旗号下的掠夺的不满。苏联时代的学界大体上也是这么说的。可以把这种解释称为“正义惩罚”说。 当时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既反感斯托雷平的政治,也反感所谓革命,不愿意渲染革命党反对斯托雷平的斗争,所以他们更相信“政府内保守派利用斯托雷平自己建立的机器杀了他自己”。博格洛夫作为奥赫拉那情报员的经历和暗杀事件前后警方的种种乖戾可疑之举和沙皇那些没心没肺的冷漠乃至冷酷言行也给人这种印象。“于是整个报刊界大声发挥对他们最有利的主题,即斯托雷平死在他亲手建立的专事反对革命的警察体制的手中。”“库尔洛夫们只不过是斯托雷平路线的产物罢了。这样一来,斯托雷平不就成了全俄间谍-奸细的始作俑者吗?斯托雷平不就成了他亲手制造奸细阴谋的牺牲品了吗?”“斯托雷平是在他幸福而快乐,满可以庆贺自己凯旋式胜利的时刻中弹身亡的。命运何以这样不宽恕人?难道没有听到手枪射击轰响后面的警告声吗?现在俄国社会可能有不流血的抗议方法,但命运可能想提醒我们,这种方法还要保留吗?”这就是“作法自毙”的解释。 索尔仁尼琴反感自由主义,更反感,他拒绝并抨击了以上两种解释。把斯托雷平捧为俄罗斯近代历史第一伟人的索翁对他的不幸结局戚戚于心无法释怀,在《红轮》写作过程中花了大量时间考证这件奇案。1976年,流亡美国的索翁在加利福尼亚古维罗夫研究所收集到斯托雷平被刺案的大量资料,同年夏秋两季在佛蒙特写成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章,同时把考证结果于1978年发表在美国一家学报上(见《红轮》第一卷索尔仁尼琴自序)。因此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红轮》中关于斯托雷平之死的说法看成史学成果,而非仅仅是文学描写。 按索翁的上述考证,博格洛夫行刺的确是出自他自己的激进思想,并非是直接受命于秘密警察或其他体制内势力,他此前为奥赫拉那做事也的确是“骗取信任”。换言之,博格洛夫的确是一名热血的革命愤青,孤胆英雄和无私的独行侠,为刺杀“革命的敌人”他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甚至不惜赔上了自己的名誉(去做警方的奸细,即便是出自“革命”动机,但只要不是“党的派遣”而是自作主张的行为,他的“同志们”仍然是不齿的)。这样的牺牲,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着实令人唏嘘。 不过,同样根据索翁提供的事实,奥赫拉那如此尽力地给他提供一切方便,难道仅仅是“受骗”?其实就像被沙皇强行终止的官方调查所显示:在此案中库尔洛夫、库利亚布科等警方负责人“不仅是办事不力,而且甚至牵涉到了间接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哪里是受骗,其实是借刀杀人,有意帮助博格洛夫完成暗杀,然后再迅速处决博格洛夫以灭口!上述所有一切怪诞现象,只有在这个逻辑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否则,以博格洛夫一介书生,高度近视,身体瘦弱,又从未做过这种杀人勾当,怎么就能一鸣惊人,一个人做到了多少革命党“组织上”做不到的事! 索翁对的“正义惩罚”说和自由主义者的“作法自毙”说都予以驳斥,但我们看到,其实他自己花费许多心血的考证毋宁说只是这两种说法的结合:博格洛夫想搞“正义惩罚”,但斯托雷平体制下的库利亚布科们借刀杀人,归根结底,斯托雷平还不是“作法自毙”吗?无怪乎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就直接把索翁的考证也列入“作法自毙”说或警方阴谋论的新进展中。 这不禁又使我们想到维特关于黑帮、红帮互变的说法:“红帮”是为“理想”走火入魔的“迷路者”,“黑帮”是“追求自私目的”的“流氓”。同样不择手段,但“红帮”是亲自杀人的“英雄”,而“黑帮”是雇凶杀人的“下流胚”。两者的鸿沟容易跨越:“红帮”一旦得势,有了既得利益,也就由“英雄”变成“流氓”了。其实索翁考证出来的这个故事更绝:连这一跨越也不需要,博格洛夫这位红帮根本还没得势,就被黑帮当了枪使,“迷路者”想当“英雄”而亲自杀人,库尔洛夫这帮“下流胚”就借刀行凶而实现“自私目的”了! 然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更大的尴尬还在于:如果他大贬维特、大褒斯托雷平的观点既不能从两人的人品道德来证明,也不能从两人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来论证,甚至不能从文化偏好来断言,那么似乎就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了。维特的朝野妥协和改革主张本来是有利于自由主义的,但自由主义反对派却不领情,不妥协的结果是维特的失败,索尔仁尼琴因此有了否定他的理由。但是同样,斯托雷平的铁腕和警察式改革主张本来是有利于沙皇政权的,但极右保皇派(以及沙皇本人)却不领情,借刀杀人的结果是斯托雷平的惨死,那么他的成功又在哪里?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斯托雷平又为什么应该得到肯定呢?维特指望的自由派不知好歹不值得指望,斯托雷平指望的沙皇“新权威”难道就知好歹,值得指望? 当然有人会说,斯托雷平本人之死不见得就是他治国主张的失败,就像商鞅虽死而“商君之法”终于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一样。不过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就在斯托雷平死前,他的改革已经显现出疲态和停滞,而斯托雷平死后仅仅6年,罗曼诺夫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还谈什么商鞅成就秦业? 然而,也许正是人亡才导致政息?索翁显然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相信,博格洛夫那两颗子弹打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俄国的国运,一亿七千万俄罗斯人的好事就这样被两枪断送了。一部《红轮》,一声长叹:如果斯托雷平不死…… 这就涉及到史学理论界的一个老争论:“如果不……”这类的讨论,即所谓的“反事实推论”,这在历史学中有意义吗? 这其实就是问历史进程是否是“必然”之道。如果历史的走向是“必然”的,一些偶然事件的有无自然无关大局,追问“如果不……”也就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历史进程是偶然的,偶然事件的有无当然非常重要,不管“如果不……”的解释显然就不是一种好的解释。 不过我的看法可能是第三种: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进程肯定不是“必然”的,但其因果关系却有相当大的实现概率,并不是掷骰子那样完全不确定。具体而言,斯托雷平在1911年的遇刺也许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斯托雷平政策的失败虽然不能说是必然,却的确是个大概率事件。即便斯托雷平不死,俄国的预后也很难比“如果维特不垮台”好,这就是我们不同意索翁“以成败论英雄”的根本理由。下一章笔者将论述“如果斯托雷平不死”,俄国又可能如何。 |